| 说起来还是有点缘由的,当年高考的几门功课中,我历史的分数最高,只是这个“最高”我到现在也不敢晒,因为一晒容易被人笑掉大牙,不过我最后上的还是中文系,毕业出来一开始去教了历史课,因为年轻,更因为历史在当年的中学里还是副课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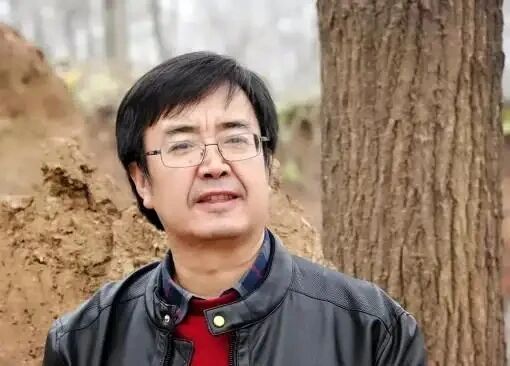
▲孙昌建 也很惭愧的,我上大一时,连汉语拼音都没有学过,所以“波坡摸福”跟ABCD是一起学的。当时对付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的主要办法,就是看连环画看电影,以速成来对付考试,以至其他系的同学都觉得中文系太轻松了,殊不知我们背《离骚》背得都要做恶梦跳江了。 也是要到后来,我才发现大多数读中文系的人,并不怎么热爱中文的,包括好多做语文老师的,对语言文字和文学也没有多少感觉的,对于他们来说,教语文和教数学教物理都是一回事情,只是一个饭碗而已,而我总是捧着一个饭碗还会想另外一个饭碗。 于是我就写诗了。 写诗能当饭吃吗?对此的回答,古今中外几乎都是一致的:不能当饭吃! 也正因为此,没有人阻拦我写诗,因为你做的是无用的事情、无功利的事情,人家才懒得理你呢,只有我实习时的一位老师,他当时真诚地劝我别写诗,还是跟他写儿童文学吧,因为这位老师当年已经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,只是后来他也去当了一名记者,这有点像我的引路者一样。 而等我明白饭碗也可以换这个道理时,我已经30岁了。为此我又开始大量地写不分行的文字,我用过几十个笔名来投稿发表文章,苍剑蓝末水东坡无肉,斯坦艾未艾秀到零点,球评影评书评,小说散文纪实,目的只有一个,不想让自己单位的领导知道,因为领导最怕员工有二心,而写作和投稿就是二心,简单说,就是有点二。 后来有人跟我说,你又成不了鲁迅,搞这么多笔名干什么,反而没人知道你是谁,也记不住你是谁,因为进入21世纪就是注意力经济了。我想想也对,倒不是说21世纪才是注意力经济,任何时代都是。我曾看过一则轶闻,一个顶流的大画家,在上世纪50年代,就不断在注意自己的名声,他每天看报纸,只要报纸上一个星期不出现他的名字,他就相当着急,就会特意打电话给朋友或报社编辑,让他们“整”一点自己的新闻出来,以引起人们的注意。 好了,以上文字只是作为背景介绍,是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点小花絮,大概都是可以删掉的,当然最好是不删,因为被删的文字往往比不删的文字要有点意思的。 回想起我为《杭州文史》写稿,也是有一点点缘由的。大约十多年前,作为文艺界的代表,我被杭州市文联推荐为市政协委员,一开始被分在提案委,因为做提案需要有点文字功夫的人,但我去了之后,发现我的文字功夫在那里实在差太远了,因为这是两套话语体系,我的文艺腔在那边是没有用的,所以一直心存惭愧,换届之时我主动要求换到文史委,因为我在想,文史不分家,或许我还能发挥一点作用。 文史委大概也看到来了个作家,且也写过几本文史类作品的,于是就把一些相关的采写撰稿任务交给我了。 我记得在《杭州文史》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《八级镗工李为民》。 跟之前的采写有所不同,以前我做了20来年的记者和编辑,所有的采写我都是单兵作战,即自己联系自己采访最后也自己成稿,但自从那次采写开始,我发现我有了“助理”,即一切都是由“助理”帮我联系好,甚至“助理”还开车接送,我采写时“助理”还在拍照片,甚至还录音做记录等等,当然成稿后“助理”也会校看补充。如此这般,既让我有点受宠若惊,又有点不太自在,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独往独来的人,这可能是长期写作养成的习惯吧,因为写作是很孤独的事情,所以好多事情也只能孤独地去做,比如说旅行,甚至是吃饭,我其实还蛮享受一个人的状态,因为这可以很任性并尽兴,虽然我是一个很随和也可以合作的人,但这并不代表我心中没有坚持和底线。 采访也是这样。老实说我在采访前都要做不少的功课,且都会自拟好20个左右的问题提纲,这样就不会被采访者牵着鼻子走,但我也有不少毛病,主要是前戏过长,闲扯太多,经常王顾左右而言他,且喜迂回包抄,不擅单刀直入,好像我的那些提纲只是规定动作,关键是要在闲扯中真正激发出对方诉说的欲望,这也的确是会有意外收获的,但也有风筝放出去收不回来的情况。 而旁边有个“助理”在,何况这个“助理”又是组织派来的,这也就是一把双刃剑,因为我以前有个理论:在办公室采访不如在会议室,在会议室不如在茶室,在茶室不如在饭桌上……为什么呢,因为这样我的主人公就不会那么正襟危坐一本正经,特别是那些做企业的领导,首先要解除他们的戒备,因为他们往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,认为哪些是可讲的,哪些是不可讲的,但在我看来,不可讲的恰恰有可能是最有价值的。所以就采访来说,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言,即使成功了十次,第十一次采访也有可能失败,因为每个采访对象都是独特的,同样是八级工,也完全是不一样的。 好在政协系统的文史类文章,主要还是“三亲史”,真实才是生命。 更为关键的是,我作为一个作家或写手,实际上还是从采写中不断学习,不时有新的收获,这就像补充能量一样,而不仅仅是完成任务。因为我发现,人到一定时候胃口就小了,尤其是不太能吸收新的能量,往往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打转,这就像习惯性的散步一样,总是有固定的路线,但是为《杭州文史》撰写文章,就感觉它还在助推我前进,让我能悟到什么是学无止境。 在采写《八级镗工李为民》之前,我对城北拱宸桥一带也是有个大概了解的,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的重工业基地,但当时对它的认识基本还是概念化的,而李为民讲到,50年代末他来杭州的时候,武林门码头、包括杭州大厦这边还是一片荒地,他们一开始就是在这片荒地上搭起了工棚,晚上就住在工棚里的。 有一点印象很深的,当时杭州要发展工业,也是急需各种人才,特别需要技术工人,李为民就是为支援杭州建设而从上海被组织派遣过来的,当时同为六级技术工,上海的工资比杭州的工资要高十几元,十几元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啊?但李为民作为从上海来支援杭州的领队,二话不说就来了,后来妻子也无怨无悔地跟着到杭州安家落户,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,这种精神不正是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吗? 通过写作这样的人物和题材,我了解到了老一辈创业者的精神世界,因为他们对杭州的贡献实在是难以估量的,而且李为民还参与制造了杭州的第一台汽轮机,这是载入史册的。 当然采访中也会有小插曲的,比如我感兴趣的是李为民的这个“八级”,是怎么一级一级评上去的,而他老人家则更喜欢讲他后来做了厂领导之后的事情,即如何带领大家开拓新局面等。 在采访李为民之后,我还采写过一位杭氧的电焊女工,也是顶尖人才,曾经代表浙江去俄罗斯核潜艇上操作过,可能因为她从事的是特珠工种,45岁就退休了,这又是让人颇为感慨的。提前退休本来是对特殊工种从业者的保护,但落实到具体一个人身上,那就酸甜苦辣都会具备的。 大概是采访工人我完成得还可以,接下去便派我去采访了两位大学教授,这就是发在《杭州文史》第十三辑的《广博精深 心怀国家:李孝聪教授谈治学历程》、十四辑的《张帆:历史很难假设,趋势可以探寻》这两篇,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。 采访李孝聪教授是在2017年11月,在杭州举办一年一度的杭州文史论坛时,当时论坛邀请北京大学的李教授来作专题讲座。我接到这个采写的任务之后,一方面是立马速补李教授的主要著作,另一方面是非常认真地听了他关于《海上丝绸之路》的讲座。这个讲座真的是太好了,帮我解开了不少疑团,即在那个无动力帆船时代,那些传教士是怎么漂洋过海到中国到杭州来的呢?正是听了李教授的讲座,让我对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也产生了兴趣,后来专门去看了他在西溪路上的墓地,也写了相关的文章。 与君一席谈,胜读十年书,跟李教授的访聊真的收获很大,主要是这些著名教授的治学观对我颇有启发,我后来想起来主要有两点,一点李教授说的是择校不如投师,他当年选择荷兰莱顿大学,而没有选那些名气更大的,因为莱顿大学在地图收藏方面是最强最为权威的;二是李教授后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,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跨学科,因为之前学历史的不碰地理,学地理的也不涉历史,两者都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,但是从李老师他们这一辈开始,就知道跨界组合了,这就出来了一门新的学科,那先行者探索者也自然就成了开山鼻祖。 还有一点是我个人的体会,即作为一个采访者一定要学得杂一点,多了解一点,否则只是傻傻地提问题,那也不会引起专家教授的重视的,在跟李教授聊他的经历时,当他提到西藏地理和荷兰人高罗佩时,我还是能够插上话的,特别是高罗佩,学文学的如果不知道这个人物,那等于不知道世界文学,这样就让李教授有了兴趣,但这里也一定要掌握好分寸,这正如在讲相声时,你的角色只是起类似捧哏的作用。 如果说李孝聪教授是师长辈的人物,那么张帆教授实际上是我的同辈,都是60后,处在相同的成长年代,这就会有较多的共同语言。 采访张帆教授也是在他来杭州讲课的间隙,当时他是北大历史系主任,后来他又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,而且有意思的是,张教授读本科时李孝聪教授就是他的老师,也正是听了李教授的建议,他才在大二时就读《资治通鉴》了。 张帆教授的强项,无疑是元史研究,但我对元史完全插不上一句话,但我对他当年成为内蒙的文科状元颇感兴趣,他当年想读北大中文系,最后因为那一年北大中文系不在内蒙招生,他就只能上历史系,那就是个“计划”的年代,而我对张教授治学的兴趣要超过他的专业,原因是我认为作为《杭州文史》的作者,同时也就是读者,我们想从这本书上看到一些什么呢?即从这些专家教授的治学史当中学到一点什么,抓到一点什么,这才是最为重要的。 比如说教授一开始也并不是对元史很有兴趣,他感兴趣的是魏晋南北朝,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元史。为什么呢?就是有着对现实的考量,特别是他能由此跟随优秀的老师学习,这就是择专业不如择师了。当然我作为一个杭州人,我们又叫《杭州文史》,那肯定要问每个教授几乎相似的问题,即你对杭州文史研究有些什么看法诸如此类的。 而我当时问张教授的是,马可·波罗时代的杭州是什么样的?还有大众传播视角下的历史,和历史学教授及专业研究者眼里的历史是不是有一定的异同? 我想我这样问的目的,一是教授们也是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,二是这也是我们的读者所决定的,记者所问的,必须是读者想问想看的,再说普罗大众学历史,不一定是先啃大部头的历史专著,他可能是从通俗读物,甚至是通过短视频和什么平台来获得的,所以我觉得对历史学者的采访,既要考虑到他的专业性,也要考虑到他的大众性,而事实上历史学者除了他的专业之外,平时喝茶聊天也跟常人无异。 这不,当时采访时我与张教授加了微信,这七八年下来也还没有披此拉黑就能说明问题了,我时常在看他转发的一些公号文章,那都是一些跟历史及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章,有的甚至还是有点敏感度的,从我转发后他的文章获得的点赞来看,那也是颇受欢迎的。 跟采访八级工相同的是,采访历史学教授,也都有“助理”帮着打理的;所不同的是,最后的记录整理者也是“助理”,这样我就要轻松多了,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来设计问题。而这几位“助理”他们都是有很好的专业背景,且文字功夫都相当不错,这几年也全都独当一面了。我平时也常看他们在《杭州文史》上的采访文章,觉得他们真是要比我们这些半路出来混的人要强多了。 这可能也意味着《杭州文史》真的架起了一座很好的桥,这是文史之桥,沟通交流之桥,也是成长成熟之桥,尤其是对我帮助更大,因为我之前主要从事文学写作,而现在算是在迈向文史之路了,虽然这还仅仅是初学。
| 

